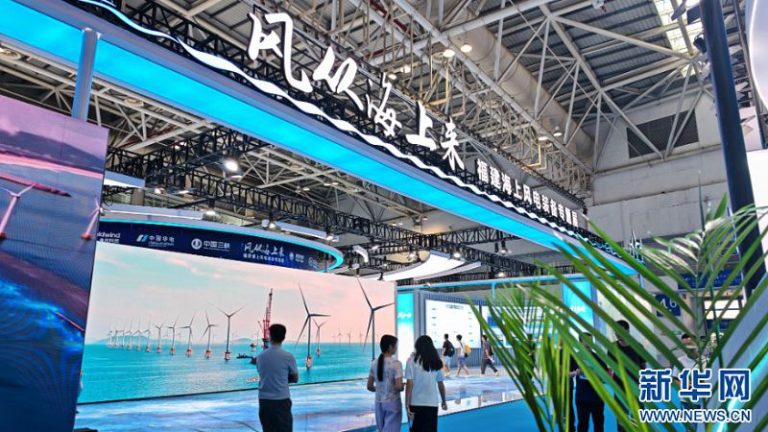白榮敏/文
太姥山位居東南海澨,作為區域女神之山,太姥信仰由來已久。但我們發現,這位上古女神太姥,後來有一個被不斷塑造的過程。到了東漢,王烈的《蟠桃記》把這位「堯時老母」演繹為被道士度化而成的仙人,並說漢武帝命東方朔授天下名山,改「母」為「姥」。這個記載告訴我們,西漢時期,中央皇權已經滲透到了太姥山地區,而在東漢,道教開始在太姥山得以發展,太姥文化已被納入中原文化體系。《太姥山全志·金石》有載:「『天下第一名山』六大字摩崖,東方朔題,鐫於摩霄庵右石壁上,字模糊不可辨。」雖然東方朔刻石的真實性值得懷疑,但這個石刻表明了人們為太姥文化尋求正統性和合法性的成功。

這種尋求並未就此停止。到了唐代,隨著太姥山佛教的發展,人們又把太姥納入了佛教神靈系統。《太姥山全志·金石》記載:「太姥墓碑:鐫曰『堯封太姥舍利寶塔』。明林祖恕記云『唐玄宗賜祭題額』,疑即此。」這8字石刻,讓傳說中已經飛昇的太姥卻有了可以安葬的「舍利」;「堯時」老母在這裡變身成為了「堯封」太姥,雖一字之差,卻顯著提高了太姥的地位。傳言唐玄宗賜祭題額,進一步表明中央皇權對太姥文化的承認、接納和吸收。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亦有載:「大姥山,在福寧州東北百里,高十餘里,週四十里,舊名才山。……唐開元中,特圖其形,敕有司春秋致祭。」
水湖瑞草堂石刻的存在表明,太姥山到了宋末元初還有道教的持續發展。這是太姥山上唯一一方元代石刻,刻於元至元庚寅年,即公元1290年,是道士楊涅生前自作的「墓誌」。石刻詳細記述了楊涅的生平,重點介紹他學道和建造石湖道宇的過程。其中楊涅買田與太姥山僧晦翁交換石刻所在這片小丘的記述,既表明了那時太姥山釋、道並存的情況,也透露了太姥山僧徒們不僅擁有如國興寺那樣恢弘的廟宇,還擁有數量不少的山地田產。
史料中記載始建於唐代的國興寺,遺址經過兩次的考古發掘,只發現宋代的遺物。大量精美絕倫的建築構件橫臥遺址之上,收穫遊客的連連驚歎。每次瞻仰,我都不禁要想,這座被明代文人讚歎為「大可擬建章,麗可比祈年」的山中佛寺,建寺者何許人?他是如何獲得政府財政的支持而建起如此龐大的廟宇?僧人們與朝廷,與地方政權,與地方大族,以及與廣大信眾如何建立良好的關係,以維持寺院香火的旺盛不衰?所有這些有趣的疑問,或許可以從那些建築構件上簡約的銘文獲得答案。

說到寺僧與地方社會的關係,我們還可以從白雲寺後石壁上的「閩藩少方伯黃公賜碑」和「遊學海題刻」的碑文中讀出寺僧們為了寺院的生存,而求助於當地政府和地方紳士,為了維護太姥寺院、僧人的權益而作出的努力。
岩石有心無口,但「石不言語最可人」,它們在等待知音,等待解讀它們的人。
太姥奇石的前身,是地底下洶湧的岩漿,是大地磅礡的心事。即便有一天,他們冷卻為僵硬的花崗岩,也沒有停止內心的悸動。經過億萬年不斷掙扎,終於有一天,掙脫出地面,山崩地裂,粉身碎骨之後,又經億萬年的風霜雪雨,成就了如今千奇百怪的面貌。這些千奇百怪的岩石,向人們傳遞雄渾的,勁健的,莊嚴的,祥和的,清奇的,淘氣的,乃至乖戾的氣息。面對太姥岩石,人們或低眉沉默,或仰頭嘯詠,甚或手舞足蹈……他們讀出了人世的悲歡,也讀出了己心的悲喜。

我想即便是空門中人,面對太姥奇石,也沒辦法做到淡然處之,一片瓦寺旁崖壁上的「玄琢奇崖」石刻該是明代高僧碧山上人對太姥奇石抑制不住的由衷讚歎。
僧人們尚且如此,善於表達的文人墨客就更加無所顧忌,他們吟詩、作賦、撰文,以特有方式記錄自身與太姥山的互動,有條件的還把作品刻在太姥山的岩石上。縱觀太姥石刻,我們可以發現,社會精英在太姥刻石的行為於明朝中後期迎來了一個高峰。原因是商品經濟的發展、人口流動的增多,為人們的出行帶來了便利,太姥山也得到了進一步的開發;士大夫階層在文化上已經趨於成熟,培養出一套符合自身趣味的審美觀和價值觀;同時禮教禁防鬆懈,個人自由意志得以充分彰顯,一部分士大夫則不滿於日漸昏暗的政治生態而寄情山水,游逸嬉玩成為時代徵候。他們登臨太姥名山,攬風觀景,吟詩作賦,勒諸石壁,正可契合他們的「風雅」趣味。
上文提及的碧山和尚,「能詩,與張叔弢友善,叔弢嘗目為詩僧。」張叔弢的好友林祖恕在《游太姥山記》中提到,他游太姥,就曾見白雲寺旁的夢堂堂後石壁有榜曰「丹室」曰「瓔珞」者,均為叔弢醉筆。張叔弢醉後於寺院題壁,真可見文人的「灑脫」和「任性」,可惜此「丹室」和「瓔珞」現均已無存。

和張叔弢一樣灑脫的還有沈儆烗。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時任福建提學副使沈儆烗與福建按察司副使兼分巡福寧道馬邦良以及福建北路參將張守貴同登太姥山,沈儆烗作《皇明萬曆庚子仲夏既望同兵憲馬公(諱邦良,富春人)參戎張公(諱守貴,福州人)登太姥》一詩,並刻石於太姥山紗帽岩。詩曰:「太姥遙臨海國寬,梯航日出望中看。夜深擊築摩霄頂,萬里風吹月影寒。」上文說張叔弢在白雲寺醉酒,這次沈儆烗一夥卻是深夜在摩霄頂擊築(一種古代樂器),明代文人們醉心山水,嗨起來的時候,一般人難以企及。

陳五昌是另外一種「任性」,太姥山上的石刻他一人居然有4處之多。萬曆三十六年(1608)春天,翰林院檢討、福清人陳五昌回鄉,當年秋天,偕文友陳仲溱同游太姥。這次遊覽,時間居然長達8天之久,對一處名山勝景的探究和迷戀,古人堪為今人示範。精英階層除了寄情山水,獲得感官和心靈的愉悅,似乎還有一種責任感,就是為名勝的傳播做點什麼,同時也為名山留下點什麼。同一時期,閩中詩壇領袖謝肇淛來了一次太姥山,離開後編了一本《太姥山志》;上文提到的馬邦良,不但修築了望仙橋,還為太姥山畫圖,他畫出圖來為太姥山作宣傳,還想給那些沒辦法親臨太姥的人們欣賞觀看。他在《〈太姥山圖〉序》中說:「余得並游會境,繪圖召鍥,俾大雅之士知有太姥,覓路尋蹤,而壤隔勢阻者,一寓目焉,亦不失宗生之臥游爾。」這次陳五昌與陳仲溱的太姥之遊,他們還為太姥山的景點命名,陳五昌的4處詩刻,也是這次遊山的成果。陳仲溱在《游太姥山記》中記述了他們的這次作為:「橋懸半空,倚岩箕踞,或舉觴大酌,翩翩欲飛,遂名橋為御風橋。伯全詩先成,命僧志其處,勒之石,因並示絕頂、岩洞諸鐫處。」

我們不由得感歎,名山之所以為名山,千百年來,就是有像馬邦良、陳五昌這樣的有心人,為太姥山文化建設貢獻自己的一點點力量,積沙成塔、集腋成裘,從而建構起了一座文化的山峰!
類似陳五昌和陳仲溱為「御風橋」命名,時任福建按察使司僉事兼福寧守巡道熊明遇也為「鴻雪洞」命名,並在洞外石壁上題刻。東坡詩曰:「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熊明遇當年在朝廷意氣風發,不曾想被捲入黨爭,從兵部外放這偏僻的福寧州,他一定志不在此,「鴻雪」二字無疑透露了他欲遠走高飛的心事。還有那方懸崖高處的「雲標」石刻,怕也是他某種心思的流露吧!「我愛此山難屢至,猶如雪上印飛鴻。」熊明遇一定是要高飛的,但這不影響他對太姥山的熱愛。當年不得意,太姥仙境正是他安頓身心的好地方。

篇幅所限,恕不一一列舉。我想,太姥石刻堪為太姥文化的「活化石」。這每一方石刻,背後都站著一個人,都連接著一個地方社會,都承載著一段歷史。刻石者當年如何來到太姥山?為什麼來到太姥山?他們與太姥山有什麼樣值得關注的聯繫?他們為什麼要在太姥山刻石?他們從哪裡來?離開太姥山又到哪裡去?……叮噹作響的刻石聲已經遠去,但鑿下的石刻卻為我們留下了一本本石質書冊、一個個窺探歷史深處有趣細節的窗口。
當我們讀太姥石刻時,我們讀什麼?無疑,這每一方石刻,都承載著一段太姥山的記憶,它們保留、豐富和見證了太姥山乃至太姥山地區歷史人文發展過程,賦予太姥自然山水以生命和靈魂,蘊涵著深刻的歷史文化和深邃的人文精神,成為太姥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流連太姥山間,瞻仰這一方方石刻,我們彷彿在聆聽太姥山滄海桑田的故事;通過這些石刻,我們得以與更多沉默的石頭對話,與一整座大山對話,欣賞它身上的風流韻致,也讀懂它背後的奧妙精微。


-中新社-150x99.jpeg)










.jpg)

-中新社-768x507.jpeg)